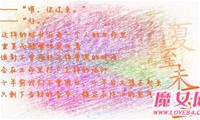梁實秋:梁實秋語錄
生吞活剝
外國的風俗永遠是有趣的,因為異國情調總是新奇的居多。新奇就有趣。不過若把異國情調生吞活剝地搬到自己家裡來,身體力行,則新奇往往變成為桎梏,有趣往往變成為肉麻。基於這種道理,很有些人至今喝茶並不加白糖與牛奶。
──《雅舍小品·洋罪》
詩難賣
詩不能賣錢。一首新詩,如拈斷數根須即能脫稿,那成本還是輕的,怕的是像牡蠣肚裡的一顆明珠,那本是一塊病,經過多久的滋潤涵養才能磨練孕育成功,寫出來到哪裡去找顧主?
──《雅舍小品·詩》
病中溫情
魯迅死前遺言“不饒怒人,
──《雅舍小品·病》
自由人
“襤褸的衣衫,是貧窮的罪過,卻是乞丐的袍褂,他的職業的優美的標識,他的財產,他的禮服,他公然出現於公共場所的服裝。……沒有人肯過問他的宗教或政治傾向。他是世界上唯一的自由人。”話雖如此,誰不到山窮水盡誰也不肯做這樣的自由人。只有一向做神仙的,如李鐵拐和濟公之類,遊戲人間的時候,才肯短期的化身為一個乞丐。
──《雅舍小品·乞丐》
柔韌之妙
莎士比亞有一名句:“‘脆弱’呀,你的名字叫做‘女人!’”但這脆弱,並不永遠使女人吃虧。越是柔韌的東西越不易摧折。
──《雅舍小品·女人》
高峰
譬如登臨,人到中年像是攀躋到了最高峰。回頭看看,一串串的小夥子正在“頭也不回呀汗也不揩”的往上爬。再仔細看看,路上有好多塊絆腳石,曾把自己磕碰得鼻青臉腫,有好多處陷阱,使自己做了若干年的井底蛙。……這種種景象的觀察,只有站在最高峰上才有可能。向前看,前面是下坡路,好走得多。
──《雅舍小品·中年》
陳釀
我看見過一些得天獨厚的男男女女,年輕的時候愣頭愣腦的,濃眉大眼,生僵挺硬,像是一些又青又澀的毛桃子,上面還帶著挺長的一層毛。他們是未經琢磨過的璞石。
──《雅舍小品·中年》
鳥的苦悶
從前我常見提籠架鳥的人,清早在街上溜達(現在這樣有閑的人少了)。我感覺興味的不是那人的悠閒,卻是那鳥的苦悶。……鳥到了這種地步,我想它的苦悶,大概是僅次於粘在膠紙上的蒼蠅,它的快樂,大概是僅優於在標本室裡住著罷?
──《雅舍小品·鳥》
不老
理想的退休生活就是真正的退休,完全擺脫賴以糊口的職務,作自己衷心所願意作的事。有人八十歲才開始學畫,也有人五十歲才開始寫小說,都有驚人的成就。“狗永遠不會老得到了不能學新把戲的地步。
──《雅舍小品續集·退休》
生氣
希臘哲學家哀皮克蒂特斯說:“計算一下你有多少天不曾生氣。在從前,我每天生氣;有時每隔一天生氣一次;後來每隔三四天生氣一次;如果你一連三十天沒有生氣,就應該向上帝獻祭表示感謝。”減少生氣的次數便是修養的結果。
──《雅舍小品續集·怒》
破落戶
每一個破落戶都可以拿了幾件舊東西來,這是不足為奇的事。國家亦然。多少衰敗的古國都有不少的古物,可以令人驚羨,欣賞,感慨,唏噓!
──《雅舍小品續集·舊》
沉默
有道之士,對於塵勞煩惱早已不放在心上,自然更能欣賞沉默的境界。這種沉默,不是話到嘴邊再咽下去,是根本沒話可說,所謂“知者不言,
──《雅舍小品續集·沉默》
會心的微笑
“蒙娜麗莎”的微笑,即是微笑,笑得美,笑得甜,笑得有味道,但是我們無法追問她為什麼笑,她笑的是什麼。……會心的微笑,只能心領神會,非文章詞句所能表達。
──《雅舍小品續集·讀畫》
能造樹麼?
又有一位詩人名Kilmer,他有一首著名的小詩──《樹》,有人批評說那首詩是“壞詩”,我倒不覺得怎麼壞,相反的“詩是像我這樣的傻瓜做的,只有上帝才能造出一棵樹”,這兩行詩頗有一點意思。人沒有什麼了不起,侈言創造,你能造出一棵樹來麼?
──《雅舍小品續集·樹》
有情樹
我曾面對著樹生出許多非非之想,覺得樹雖不能言,不解語,
──《雅舍小品續集·樹》
吃一行恨一行
有人只看見和尚吃饅頭,沒看見和尚受戒,遂生羡慕別人之心,以為自己這一行只有苦沒有樂,不但自己唉聲歎氣,恨自己選錯了行,還會諄諄告誡他的子弟千萬別再做這一行。這叫做“吃一行,恨一行”。
──《雅舍散文二集·流行的謬論》
無斧鑿痕
藝術與自然本是相對的名詞。凡是藝術皆是人為的。西諺有雲:Ars est celare artem(真藝術不露人為的痕跡),猶如吾人所謂“無斧鑿痕”。
──《雅舍散文二集·盆景》
戕害生機
我看過一些盆景,鉛鐵絲尚未除去,好像是五花大綁,即或已經解除,樹皮上也難免皮開肉綻的疤痕。這樣藝術的製作,對於植物近似戕害生機的桎梏。我常在欣賞盆景的時候,聯想到在遊藝場中看到的一個患侏儒症的人,穿戴齊整的出現在觀眾面前,博大家一笑。又聯想到從前婦女的纏足,纏得趾骨彎折,以成為三寸金蓮,作搖曳婀娜之態!
──《雅舍散文二集·盆景》
天性
古聖先賢,無不勸孝。其實孝也是人性的一部分,也是自然的,否則勸亦無大效。父母女間的相互的情愛都是天生的。不但人類如此,一切有情莫不皆然。我不大敢信禽獸之中會有梟獍。
──《雅舍散文二集·父母的愛》
代溝
自從人有老少之分,老一代與少一代之間就有一道溝,可能是難以飛渡深溝天塹,也可能是一步邁過的小瀆陰溝,總之是其間有個界限。溝這邊的人看溝那邊的人不順眼,溝那邊的人看溝這邊的人不像話,也許吹鬍子瞪眼,也許拍桌子卷袖子,也許口出惡聲,也許真個的鬧出命案,看雙方的氣質和修養而定。
──《雅舍小品三集·代溝》
福到了
暴發戶對於室內裝潢是相當考究的。進得門來,迎面少不得一個特大號的紅地灑金的福字斗方,是倒掛曆著的,表示福到了。如果一排五個斗方,當然更好,那些是五福臨門。
──《雅舍小品三集·暴發戶》
大主意自己拿
人,誠如波斯詩人莪謨伽耶瑪所說,來不知從何處來,去不知向何處去,來時並非本願,去時亦未征得同意,糊裡糊塗地在世間逗留一段時間。在此期間內,我們是以心為形役呢?還是立德立功立言以求不朽呢?還是參究生死直超三界呢?這大主意需要自己拿。──《秋室雜文·談時間》
人需友誼
只有神仙與野獸才喜歡孤獨,人是要朋友的。
──《秋室雜文·談友誼》
朋友
佛蘭克林說:“有三個朋友是忠實可靠的──老妻,老狗與現款。”妙的是這三個朋友都不是朋友。倒是亞里斯多德的一句話最乾脆:“我的朋友啊!世界上根本沒有朋友。”這些話近於憤世嫉俗,事實上世界裡還是有朋友的,不過雖然無需打著燈籠去找,卻是像沙裡淘金而且還需要長時間地洗煉。一旦真鑄成了友誼,便會金石同堅,永不退轉。
──《秋室雜文·談友誼》
止痛片
其實哪一個人在人生的坎坷的路途上不有過顛躓?哪一個不再憧憬那神聖的自由的快樂的境界?不過人生的路途就是這個樣子,抱怨沒有用,逃避不可能,想飛也只是一個夢想。人作畫是現實的,現實的人生還需要現實的方法去處理。偶然作個白晝夢,想入非非,任想像去馳騁,獲得一進的慰安,當然亦無不可,但是這究竟只是一時有效的鎮定劑,可以暫止痛,但不根本治療。
──《談徐志摩》
薔薇與荊棘
人生的路途,多少年來就這樣地()踐踏出來了,人人都循著這路途走,你說它是薔薇之路也好,你說它是荊棘之路也好,反正你得乖乖地把它走完。
──《談徐志摩》
玩
人從小到老都是一直在玩,不過玩具不同。小時候玩假刀假槍,長大了服兵役便真刀真槍;小時候一角一角地放進豬形儲蓄器,長大了便一張一張支票送進銀行;小時候玩“過家家”,“攙新娘子”,長大了便真個的娶妻生子成家立業。有人玩筆桿,有人玩鈔票,有人玩古董,有人玩政治,都是玩。
──《西雅圖雜記·模型》
梁實秋:同學
同學,和同鄉不同。只要是同一鄉里的人,便有鄉誼。同學則一定要有同窗共硯的經驗,在一起讀書,在一起淘氣,在一起挨打,才能建立起一種親切的交情,尤其是日後回憶起來,別有一番情趣。縱不曰十年窗下,至少三、五年的聚首總是有的。從前書房狹小,需要大家擠在一個窗前,窗間也許著一雞籠,所以書房又名曰雞窗。至於幫硬死沉的硯臺,大家共用一個,自然是經濟合理。
自有學校以來,情形不一樣了。動輒幾十人一班,百多人一級,一批一批的畢業,像是蒸鍋鋪的饅頭,一屜一屜的發售出去。他們是一個學校的畢業生,畢業的時間可能相差幾十年。祖父和他的兒孫可能是同一學校畢業,但是不便稱為同學。彼此相差個十年八年的,在同一學校裡根本沒有碰過頭的人,只好勉強解嘲自稱為先後同學了。
小時候的同學,幾十年後還能知其下落的恐怕不多。我小學同班的同學二十余人,現在記得姓名的不過四、五人。其中年齡較長身材最高的一位,我永遠不能忘記,他腦後半長的頭髮用紅頭繩緊密紮起的小辮子,在腦後挺然翹起,像是一根小紅蘿蔔。他善吹喇叭,畢業後投步軍統領門當兵,在“堆子”前面站崗,拄著上刺刀的步槍,滿神氣的。有一位滿臉疙瘩嚕嗦,大家送他一個綽號“小炸丸子”,人緣不好,偏愛惹事,有一天犯了眾怒,幾個人把他抬上講臺,按住了手腳,扯開他的褲帶,每個人在他褲襠裡吐一口唾液!我目睹這驚人的暴行,難過很久。又有一位好奇心強,見了什麼東西都喜歡動手,有一天遲到,見了老師為實驗冷縮熱漲的原理剛燒過的一隻鐵球,過去一把抓起,大叫一聲,手掌燙出一片的溜漿大泡。功課最好寫字最工的一位,規行矩步,主任老師最賞識他,畢業後,於某大書店分行由學徒做到經理。再有一位由辦事員做到某部司長。此外則人海茫茫,我就都不知其所終了。
有人成年之後怕看到小時候的同學,因為他可能看見過你一脖子泥、鼻涕過河往袖子上抹的那副髒相,他也許看見過你被罰站、打手板的那副窘相。他知道你最怕人知道你的乳名,不是“大和尚”就是“二禿子”,不是“栓子”就是“大柱子”,他會冷不防的在大庭廣眾之中猛喊你的乳名。使你臉紅。不過我覺得這也沒有什麼不好。小時候嬉嬉鬧鬧,天真率直,那一段純稚的光景已一去而不可複得,如果長大之後還能邂逅一兩個總角之交,勾起童時的回憶,不也快慰生平麼?
我進了中學便住校,一住八年。同學之中有不少很要好的,友誼保持數十年不墜,也有因故翻了臉扭過脖子的。大多數只是在我心中留下一個面貌謦欬的影子。我那一級同學有八、九十人,經過八年時間的淘汰過濾,畢業時僅得六、七十人,而我現在記得姓名的約六十人。其中有早夭的,有因為一時糊塗順手牽羊而被開除的,也有不知什麼原故忽然輟學的,而這剩下的一批,畢業之後多年來天各一方,大概是“動如參與商”了。我三十八年來臺灣,數同級的同學得十余人,我們還不時的杯酒聊歡,恰滿一桌。席間,無所不談。談起有一位綽號“燒餅”,因為他的頭扁而圓,取其形似。在體育館中他翻雙杠不慎跌落,旁邊就有人高呼:“留神芝麻掉了!”燒餅早已不在,不死于抗戰之時,而死于勝利之日,不死於敵人之手,而死于同胞之刀,談起來大家無不欷歔。又談起一位綽號“臭豆腐”,只因他上作文課,卷子上塗抹之處太多,東一團西一塊的盡是墨豬,老師看了一皺眉頭說:“你寫的是什麼字,漆黑一塊塊的,像臭豆腐似的!”哄堂大笑,(北方的臭豆腐是黑色的,方方的小塊)於是臭豆腐的綽號不脛而走。如今大家都做了祖父,這樣的稱呼不雅,同人公議,摘除其中的一個臭字,簡稱他為豆腐,直到如今。還有一位綽號叫“火車頭”,因為他性偏急,出語如連珠炮,氣咻咻,唾沫飛濺,作事橫衝直撞,勇猛向前,所以贏得這樣的一個綽號,抗戰期間不幸死於日寇之手。我們在台的十幾個同學,輪流做東,宴會了十幾次,以後便一個個的凋謝,潰不成軍,湊不起一桌了。
同學們一出校門,便各奔前程。因修習的科目不同,活動的範圍自異。風雲際會,拖青紆紫者有之;踵武陶朱,腰纏萬貫者有之;有一技之長,出人頭地者有之;而座擁皋比,以至於吃不飽餓不死者亦有之。在校的時候,品學俱佳,頭角崢嶸,以後未必有成就。所謂“小時了了,大未必佳”,確是不刊之論。不過一向為人卑鄙投機取巧之輩,以後無論如何翻雲覆雨,也逃不過老同學的法眼。所以有些人回避老同學惟恐不及。
杜工部漂泊西南的時候,歎()老嗟貧,詠出“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裘馬自輕肥”的句子。那個“自”字好不令人慘然!好像是袞袞諸公裘馬輕肥,就是不管他“一家都在秋風裡”。其實同學少年這一段交誼不攀也罷。“衣敝溫袍,與衣狐貉者立”,縱然不以為恥,可是免不了要看人的嘴臉。
樹皮上也難免皮開肉綻的疤痕。這樣藝術的製作,對於植物近似戕害生機的桎梏。我常在欣賞盆景的時候,聯想到在遊藝場中看到的一個患侏儒症的人,穿戴齊整的出現在觀眾面前,博大家一笑。又聯想到從前婦女的纏足,纏得趾骨彎折,以成為三寸金蓮,作搖曳婀娜之態!──《雅舍散文二集·盆景》
天性
古聖先賢,無不勸孝。其實孝也是人性的一部分,也是自然的,否則勸亦無大效。父母女間的相互的情愛都是天生的。不但人類如此,一切有情莫不皆然。我不大敢信禽獸之中會有梟獍。
──《雅舍散文二集·父母的愛》
代溝
自從人有老少之分,老一代與少一代之間就有一道溝,可能是難以飛渡深溝天塹,也可能是一步邁過的小瀆陰溝,總之是其間有個界限。溝這邊的人看溝那邊的人不順眼,溝那邊的人看溝這邊的人不像話,也許吹鬍子瞪眼,也許拍桌子卷袖子,也許口出惡聲,也許真個的鬧出命案,看雙方的氣質和修養而定。
──《雅舍小品三集·代溝》
福到了
暴發戶對於室內裝潢是相當考究的。進得門來,迎面少不得一個特大號的紅地灑金的福字斗方,是倒掛曆著的,表示福到了。如果一排五個斗方,當然更好,那些是五福臨門。
──《雅舍小品三集·暴發戶》
大主意自己拿
人,誠如波斯詩人莪謨伽耶瑪所說,來不知從何處來,去不知向何處去,來時並非本願,去時亦未征得同意,糊裡糊塗地在世間逗留一段時間。在此期間內,我們是以心為形役呢?還是立德立功立言以求不朽呢?還是參究生死直超三界呢?這大主意需要自己拿。──《秋室雜文·談時間》
人需友誼
只有神仙與野獸才喜歡孤獨,人是要朋友的。
──《秋室雜文·談友誼》
朋友
佛蘭克林說:“有三個朋友是忠實可靠的──老妻,老狗與現款。”妙的是這三個朋友都不是朋友。倒是亞里斯多德的一句話最乾脆:“我的朋友啊!世界上根本沒有朋友。”這些話近於憤世嫉俗,事實上世界裡還是有朋友的,不過雖然無需打著燈籠去找,卻是像沙裡淘金而且還需要長時間地洗煉。一旦真鑄成了友誼,便會金石同堅,永不退轉。
──《秋室雜文·談友誼》
止痛片
其實哪一個人在人生的坎坷的路途上不有過顛躓?哪一個不再憧憬那神聖的自由的快樂的境界?不過人生的路途就是這個樣子,抱怨沒有用,逃避不可能,想飛也只是一個夢想。人作畫是現實的,現實的人生還需要現實的方法去處理。偶然作個白晝夢,想入非非,任想像去馳騁,獲得一進的慰安,當然亦無不可,但是這究竟只是一時有效的鎮定劑,可以暫止痛,但不根本治療。
──《談徐志摩》
薔薇與荊棘
人生的路途,多少年來就這樣地()踐踏出來了,人人都循著這路途走,你說它是薔薇之路也好,你說它是荊棘之路也好,反正你得乖乖地把它走完。
──《談徐志摩》
玩
人從小到老都是一直在玩,不過玩具不同。小時候玩假刀假槍,長大了服兵役便真刀真槍;小時候一角一角地放進豬形儲蓄器,長大了便一張一張支票送進銀行;小時候玩“過家家”,“攙新娘子”,長大了便真個的娶妻生子成家立業。有人玩筆桿,有人玩鈔票,有人玩古董,有人玩政治,都是玩。
──《西雅圖雜記·模型》
梁實秋:同學
同學,和同鄉不同。只要是同一鄉里的人,便有鄉誼。同學則一定要有同窗共硯的經驗,在一起讀書,在一起淘氣,在一起挨打,才能建立起一種親切的交情,尤其是日後回憶起來,別有一番情趣。縱不曰十年窗下,至少三、五年的聚首總是有的。從前書房狹小,需要大家擠在一個窗前,窗間也許著一雞籠,所以書房又名曰雞窗。至於幫硬死沉的硯臺,大家共用一個,自然是經濟合理。
自有學校以來,情形不一樣了。動輒幾十人一班,百多人一級,一批一批的畢業,像是蒸鍋鋪的饅頭,一屜一屜的發售出去。他們是一個學校的畢業生,畢業的時間可能相差幾十年。祖父和他的兒孫可能是同一學校畢業,但是不便稱為同學。彼此相差個十年八年的,在同一學校裡根本沒有碰過頭的人,只好勉強解嘲自稱為先後同學了。
小時候的同學,幾十年後還能知其下落的恐怕不多。我小學同班的同學二十余人,現在記得姓名的不過四、五人。其中年齡較長身材最高的一位,我永遠不能忘記,他腦後半長的頭髮用紅頭繩緊密紮起的小辮子,在腦後挺然翹起,像是一根小紅蘿蔔。他善吹喇叭,畢業後投步軍統領門當兵,在“堆子”前面站崗,拄著上刺刀的步槍,滿神氣的。有一位滿臉疙瘩嚕嗦,大家送他一個綽號“小炸丸子”,人緣不好,偏愛惹事,有一天犯了眾怒,幾個人把他抬上講臺,按住了手腳,扯開他的褲帶,每個人在他褲襠裡吐一口唾液!我目睹這驚人的暴行,難過很久。又有一位好奇心強,見了什麼東西都喜歡動手,有一天遲到,見了老師為實驗冷縮熱漲的原理剛燒過的一隻鐵球,過去一把抓起,大叫一聲,手掌燙出一片的溜漿大泡。功課最好寫字最工的一位,規行矩步,主任老師最賞識他,畢業後,於某大書店分行由學徒做到經理。再有一位由辦事員做到某部司長。此外則人海茫茫,我就都不知其所終了。
有人成年之後怕看到小時候的同學,因為他可能看見過你一脖子泥、鼻涕過河往袖子上抹的那副髒相,他也許看見過你被罰站、打手板的那副窘相。他知道你最怕人知道你的乳名,不是“大和尚”就是“二禿子”,不是“栓子”就是“大柱子”,他會冷不防的在大庭廣眾之中猛喊你的乳名。使你臉紅。不過我覺得這也沒有什麼不好。小時候嬉嬉鬧鬧,天真率直,那一段純稚的光景已一去而不可複得,如果長大之後還能邂逅一兩個總角之交,勾起童時的回憶,不也快慰生平麼?
我進了中學便住校,一住八年。同學之中有不少很要好的,友誼保持數十年不墜,也有因故翻了臉扭過脖子的。大多數只是在我心中留下一個面貌謦欬的影子。我那一級同學有八、九十人,經過八年時間的淘汰過濾,畢業時僅得六、七十人,而我現在記得姓名的約六十人。其中有早夭的,有因為一時糊塗順手牽羊而被開除的,也有不知什麼原故忽然輟學的,而這剩下的一批,畢業之後多年來天各一方,大概是“動如參與商”了。我三十八年來臺灣,數同級的同學得十余人,我們還不時的杯酒聊歡,恰滿一桌。席間,無所不談。談起有一位綽號“燒餅”,因為他的頭扁而圓,取其形似。在體育館中他翻雙杠不慎跌落,旁邊就有人高呼:“留神芝麻掉了!”燒餅早已不在,不死于抗戰之時,而死于勝利之日,不死於敵人之手,而死于同胞之刀,談起來大家無不欷歔。又談起一位綽號“臭豆腐”,只因他上作文課,卷子上塗抹之處太多,東一團西一塊的盡是墨豬,老師看了一皺眉頭說:“你寫的是什麼字,漆黑一塊塊的,像臭豆腐似的!”哄堂大笑,(北方的臭豆腐是黑色的,方方的小塊)於是臭豆腐的綽號不脛而走。如今大家都做了祖父,這樣的稱呼不雅,同人公議,摘除其中的一個臭字,簡稱他為豆腐,直到如今。還有一位綽號叫“火車頭”,因為他性偏急,出語如連珠炮,氣咻咻,唾沫飛濺,作事橫衝直撞,勇猛向前,所以贏得這樣的一個綽號,抗戰期間不幸死於日寇之手。我們在台的十幾個同學,輪流做東,宴會了十幾次,以後便一個個的凋謝,潰不成軍,湊不起一桌了。
同學們一出校門,便各奔前程。因修習的科目不同,活動的範圍自異。風雲際會,拖青紆紫者有之;踵武陶朱,腰纏萬貫者有之;有一技之長,出人頭地者有之;而座擁皋比,以至於吃不飽餓不死者亦有之。在校的時候,品學俱佳,頭角崢嶸,以後未必有成就。所謂“小時了了,大未必佳”,確是不刊之論。不過一向為人卑鄙投機取巧之輩,以後無論如何翻雲覆雨,也逃不過老同學的法眼。所以有些人回避老同學惟恐不及。
杜工部漂泊西南的時候,歎()老嗟貧,詠出“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裘馬自輕肥”的句子。那個“自”字好不令人慘然!好像是袞袞諸公裘馬輕肥,就是不管他“一家都在秋風裡”。其實同學少年這一段交誼不攀也罷。“衣敝溫袍,與衣狐貉者立”,縱然不以為恥,可是免不了要看人的嘴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