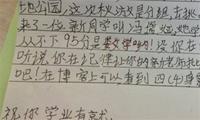泰戈爾:最後一封信
由於我的過錯,空蕩蕩的寓所憤懣地扭過臉不看我。
我從一間屋子走到另一間屋子,沒有一塊屬於我的地方。
我悶悶不樂地走到外面。
我決計出租房子,搬到特拉登去。
由於過分悲愴,我許久不敢進阿姆麗的房間。可是房客快來了,房間得打掃一下。我只得開了她上鎖的房門。
房間裡有她一雙阿格拉①繡花拖鞋、梳子、裝著洗髮液、護膚液的幾個瓶子。書架上陳放著她的課本,一架小手風琴,一本剪貼簿貼滿她收集的照片。衣架上掛著長毛巾、上衣、機織布紗麗。小玻璃櫃裡是各種玩具、空粉盒。
我坐在桌後的床板上,從她的紅皮書包裡取出一本算術練習本,一封未封的信掉了下來。信封上寫著我的地址,是阿姆麗稚嫩的字體。
我聽說,人溺死的那一刻,眼前閃現濃縮的一生。我仿佛是個淹死的人,拿信的一瞬間,許多往事紛至遝來。
阿姆麗媽媽去世那年,她剛七歲。
我莫名其妙地擔心她也活不了很久。
因為,她神情憂鬱,過早訣別的陰影從未來倏忽飛來,籠罩著她一雙烏黑的大眼睛。
我不敢讓她離開我一步。坐在辦公室裡做事,唯恐突然發生不測。
她姨媽從班基普爾來度假,憂慮地說:“外甥女學習要耽誤了。如今誰樂意娶個目不識丁的女孩,當作包袱頂在頭上?”
我好生愧疚,說:“明天我帶她到貝都恩學校報名。
第二天,她上學了,不過放假的日子大大超過上課的日子。她父親經常參與讓送她上學的汽車倒開回來的陰謀。
第二年,她姨媽又來度假,見此情形,大為不滿:“這樣念書不行!我得把她帶走,送她上貝那勒斯的寄宿學校。我無論如何要把她從父親的溺愛中解救出來。”
她跟她姨媽走了,因為我應允,她是懷著一腔無淚的怨惱走的。
我出門遊覽巴特裡那塔聖地,從自己煩悶的心境裡逃了出來。四個月沒有得到她的消息,以為老師的關懷已消解她心頭的壘塊。
我心上的一塊石()頭落了地,我暗暗慶倖把她託付給了“大神”。四個月後回來,我徑直前往貝那勒斯看望阿姆麗。途中收到一封信——還說什麼,大神已收下她了!
一切都過去了。
我坐在阿姆麗的房間裡展開信紙,只見上面寫著:我很想見您。
沒有別的話。
泰戈爾:兒童聖地10
一束陽光斜照著柴扉。
聚集的人仿佛在血管裡聽見洪荒年代創造的偈語:母親,開門!
門開了。
母親懷抱著嬰兒坐在草榻上。
等待著陽光照臨朝霞懷抱的啟明星似的嬰兒的臉。
詩人彈琴,歌聲在天空飄繞——勝利屬於人類,屬於新生兒,屬於永生的人。
君主、乞丐()、雅士、罪人、才子、愚氓……一齊雙膝跪地,齊聲歡呼:“勝利屬於人類!屬於新生兒!屬於永生的人!”
泰戈爾:廢紙簍
“你在幹什麼,蘇妮①?”父親吃驚地問,“幹嗎把衣服裝在皮箱裡?你要去哪兒?”
蘇娜麗達的臥室在三樓,有兩扇南窗。窗戶前床上鋪著考究的拉克惱床單,對面靠牆的書桌上,擺著亡母的遺像,
妹妹莎米達抱膝而坐,側臉望著窗外,她沒有梳頭,眼圈紅紅的,顯然剛才哭過。
蘇娜麗達不答話,只管低頭整理衣服,手微微發顫。
“你要出門?”父親又問。
蘇娜麗達口氣生硬地說:“你講過,我不能在家裡成親,我到阿努②家去。”
“啊呀!”莎米達叫起來,“姐姐,你胡說什麼呀!”
父親露出惱怒而又無可奈何的神色:“他家裡人不同意我們的觀點。”
“但他們的意見,我得一輩子聽從。”女兒語氣堅定,表情肅穆,決心不可動搖,
父親憂心忡忡:“阿尼爾的父親鼓吹種姓制度,會同意你倆的婚事?”
“您不瞭解阿尼爾,”女兒自豪地說,“他是個有主見、胸懷坦蕩的青年。”
父親長歎一聲,莎米達挽著父親的胳膊走了。
鐘敲了十二下。
蘇娜麗達一上午沒有吃飯。莎米達來叫過一回,可她非要到朋友家吃不可。
失去母愛的蘇娜麗達是父親的掌上明珠。他也要進屋勸女兒吃飯,莎米達拉住他說:“別去了,爸爸,她說不吃是決不會吃的。”
蘇娜麗達把頭伸到窗外,朝大街上張望。終於,阿尼爾家的汽車開來了。她急忙梳妝,一枚精巧的胸針插在胸前。
“拿去,阿尼爾家的信。”莎米達把一封信丟在姐姐懷裡。
蘇娜麗達讀完信,面如死灰,頹然坐在大木箱上。
阿尼爾在信中寫道:我原以為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改變父親的觀點,豈料磨破嘴唇,他仍固執己見,所以……下午一點。
蘇娜麗達呆坐著,眼裡沒有淚水。
僕人羅摩查裡塔進屋低聲說:“他家的汽車還在樓下呢。”
“叫他們滾!”蘇娜麗達一聲怒吼。
她養的狗默默地趴在她腳邊。
父親得知事情發生突變,沒有細問,撫摸著女兒的柔軟的頭髮說:“蘇妮,走,到赫桑巴特你舅舅家散散心。”
明天舉行阿尼爾的婚禮。
阿尼爾執拗地叫嚷:“不,我不結婚。”
母親心疼地歎氣:“唉,依了他吧。”
“你瘋啦!”父親勃然大怒。
家裡張燈結綵,嗩呐從早晨吹到晚上。
阿尼爾失魂落魄。
傍晚七點左右,蘇娜麗達家的一樓裡點著煤油燈,污漬斑斑的地毯上摞著一疊報紙。管家卡伊拉斯·薩爾加爾左手托著水煙筒抽煙,右手呱嗒呱嗒扇著蒲扇,他正等聽差來為他按摩酸痛的大腿。
阿尼爾突然來臨。
管家慌忙起身,抻抻衣服。
“忙亂之中忘了給()喜錢,想起了特地來一趟。”阿尼爾猶豫一下說,“我想順便再看一眼你家蘇娜麗達小姐的臥室。”
阿尼爾慢步走進臥室,坐在床上,雙手抱著腦袋。床具上,門框上,窗簾上,漾散著人昏迷呻喚般的幽微的氣味,是柔發的?殘花的?抑或是空寂的臥室裡珍藏的回憶的?不得而知。
阿尼爾抽了會兒煙,把煙蒂往窗外一擲,從書桌底下取出廢紙簍,捧在胸前。他的心猛地抽搐一下。他看見滿簍是撕碎的信紙。淡藍的信紙上是他的筆跡。此外還有一張照片的碎片,四年前用紅綢帶系在硬紙板上的兩朵花——枯萎了的三色堇和紫羅蘭。
右手呱嗒呱嗒扇著蒲扇,他正等聽差來為他按摩酸痛的大腿。阿尼爾突然來臨。
管家慌忙起身,抻抻衣服。
“忙亂之中忘了給()喜錢,想起了特地來一趟。”阿尼爾猶豫一下說,“我想順便再看一眼你家蘇娜麗達小姐的臥室。”
阿尼爾慢步走進臥室,坐在床上,雙手抱著腦袋。床具上,門框上,窗簾上,漾散著人昏迷呻喚般的幽微的氣味,是柔發的?殘花的?抑或是空寂的臥室裡珍藏的回憶的?不得而知。
阿尼爾抽了會兒煙,把煙蒂往窗外一擲,從書桌底下取出廢紙簍,捧在胸前。他的心猛地抽搐一下。他看見滿簍是撕碎的信紙。淡藍的信紙上是他的筆跡。此外還有一張照片的碎片,四年前用紅綢帶系在硬紙板上的兩朵花——枯萎了的三色堇和紫羅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