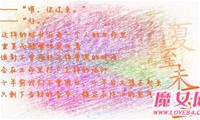《詩經:白駒》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
縶之維之,以永今朝。
所謂伊人,於焉逍遙?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
縶之維之,以永今夕。
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
爾公爾侯,逸豫無期?
慎爾優遊,勉爾遁思。
皎皎白駒,在彼空穀。
生芻一束,其人如玉。
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注釋:
1、皎皎:毛色潔白貌。
2、場:菜園。
3、縶:用繩子絆住馬足。維:拴馬的韁繩,此處意為維繫,用作動詞。
4、永:長。此處用如動詞。
5、伊人:那人,指白駒的主人。
6、於焉:在此。
7、藿:豆葉。
8、賁然:馬放蹄急馳貌。賁,通“奔”。思:語助詞。
9、爾:你,即“伊人”。公、侯:古爵位名,此處皆作動詞,為公為侯之意。
10、逸豫:安樂。無期:沒有終期。
11、慎:慎重。優遊:義同“逍遙”。
12、勉:“免”之假借字,打消之意。遁:避世。
13、空穀:深谷。空,“穹”之假借。
14、生芻:青草。
15、其人:亦即“伊人”。如玉:品德美好如玉。
16、金玉:此處皆用作意動詞,珍惜之意。
17、遐心:疏遠之心。
譯文:
馬駒毛色白如雪,吃我菜園嫩豆苗。
絆住馬足拴韁繩,盡情歡樂在今朝。
心想賢人終來臨,在此作客樂逍遙。
馬駒毛色白如雪,吃我菜園嫩豆葉。
絆住馬足拴韁繩,盡情歡樂在今夜。
心想賢人終來臨,在此作客心意愜。
馬駒毛色白如雪,風馳電掣飄然至。
應在朝堂為公侯,為何安樂無終期。
優遊度日宜謹慎,避世隱遁太可惜。
馬駒毛色白如雪,空曠深谷留身影。
喂馬一束青青草,那人品德似瓊英。
音訊不要太自珍,切莫疏遠忘友情。
賞析:
《白駒》一,《毛詩序》以為是大夫刺宣王不能留用賢者於朝廷。從詩本身看不出有這一層意思。朱熹《詩集傳》說:“為此詩者,以賢者之去而不可留。”出語較有迴旋之餘地。明清以後,有人認為殷人尚白,大夫乘白駒,為武王餞送箕子之詩;有人認為是王者欲留賢者不得,因而放歸山林所賜之詩。然而漢魏時期,蔡邕《琴操》就說:“《白駒》者,失朋友之所作也。”曹植《釋思賦》也有:“彼朋友之離別,猶求思乎白駒”之句。蔡、曹二人都認為這是一首有關朋友離別的詩。今人余冠英《詩經選》以為是留客惜別的詩,其說上承蔡、曹,較合詩意。
全詩四章分為兩個層次。前三章為第一層,寫客人未去主人挽留。古代留客的方式多種多樣。《漢書-陳遵傳》載有“投轄于井”的方式,
由上文所述可知,此詩形象鮮明,栩栩如生,給讀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刻畫人物手法靈活多變,直接描寫和間接描寫交相使用,值得玩味。孫鑛評曰:“寫依依不忍舍之意,溫然可念,風致最有餘。”
《詩經:黃鳥·黃鳥黃鳥》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
無啄我粟。
此邦之人,不我肯穀。
言旋言歸,複我邦族。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
無啄我粱。
此邦之人,不可與明。
言旋言歸,複我諸兄。
黃鳥黃鳥,無集於栩,
無啄我黍。
此邦之人,不可與處。
言旋言歸,複我諸父。
注釋:
1、黃鳥:黃雀。
2、榖:木名,即楮木。
3、穀:養育。“不我肯穀”即“不肯穀我”。
4、言:語助詞,無實義。旋:通“還”,回歸。
5、複:回去。邦:國。族:家族。
6、明:通“盟”,
7、栩:柞樹。
譯文:
黃鳥黃鳥你聽著,不要聚在榖樹上,
別把我的粟啄光。
住在這個鄉的人,如今拒絕把我養。
常常思念回家去,回到親愛的故鄉。
黃鳥黃鳥你聽著,不要桑樹枝上集,
不要啄我黃粱米。
住在這個鄉的人,不可與他講誠意。
常常思念回家去,與我兄弟在一起。
黃鳥黃鳥你聽著,不要聚在柞樹上,
別把我的黍啄光。
住在這個鄉的人,不可與他相處長。
常常思念回家去,回到我的父輩旁。
賞析:
《小雅-黃鳥》是人為苦難人民喊出的悲憤之聲:黃鳥呀黃鳥,你這貪得無厭的東西,你為什麼吃光了我的糧食,還要跟我作對。你停在我家門前的樹上,叫得人心煩。你這惡鳥!簡直就像是這淒涼人世間心狠手辣、卑鄙無恥者的幫兇。我們懷著殷切的希望,
聽著這來自遠古的動人心魄、直沖雲霄的憤怒悲慟的呼聲,就連今天的人也禁不住為這位生活於亂離之世的詩人的不幸遭遇灑一掬同情之淚了。文學是活的社會生活與心靈體驗的歷史,《小雅-黃鳥》這首詩,正是春秋末葉社會政治腐敗、經濟衰退、世風日下之壞亂景象的一個極具典型意義的縮影。作者在這裡所要表達的是一種不堪忍受剝削和壓榨的憤怒和對世道人心的徹底絕望。
在立意方面,這首詩與《魏風-碩鼠》有異曲同工之妙:即以“啄我之粟”的黃鳥發端,類比起興,以此影射“不可與處”的“此邦之人”,既含蓄生動,又表現了強烈的愛憎感情。
值得注意的是,此詩與《我行其野》,前人多以為出自同時,是周宣王末年禮崩樂壞、社會風氣惡化的表現。王質《詩總聞》論《我行其野》說:“觀此詩,然後知前詩(《黃鳥》)之所以不可與處者也。二詩當出一人。”此說雖未必,但也說明了二詩主題的相關性。舊說如《毛詩序》謂詩旨為“刺宣王”,毛傳雲:“(周)宣王之末,天下室家離散,妃匹相去,有不以禮者”,鄭箋雲:“刺其以陰禮(男女之禮)教親而不至,聯兄弟之不固。”今人多不取。而朱熹《詩集傳》雲:“民適異國不得其所,故作此詩。”差為得之。
《詩經:祈父》
祈父,予王之爪牙。
胡轉予於恤,靡所止居?
祈父,予王之爪士。
胡轉予於恤,靡所厎止?
祈父,亶不聰。
胡轉予於恤?有母之屍饔。
注釋:
1、祈父:周代掌兵的官員,即大司馬。
2、恤:憂愁。
3、靡所:沒有處所。
4、厎:停止。
5、亶:確實。聰:聽覺靈敏。
6、屍:借為“失”。饔:熟食。
譯文:
司馬!我是君王的衛兵。
為何讓我去征戍?沒有住所不安定。
司馬!我是君王的武士。
為何讓我去征戍?跑來跑去無休止。
司馬!腦子的確不好使。
為何讓我去征戍?家中老母沒飯吃。
賞析:
《祈父》是周王朝的王都衛士(相當於後代的御林軍)抒發內心不滿情緒的。《毛詩序》說:“《祈父》,刺宣王也。”鄭箋補充說:“刺其用祈父不得其人也。”朱熹《詩集傳》引呂祖謙語說:“越句踐伐吳,有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皆遣歸;魏公子無忌救趙,亦令獨子無兄弟者歸養。則古者有親老而無兄弟,其當免征役,必有成法,故責司馬之不聰”,“責司馬者,不敢斥王也。”方玉潤《詩經原始》徑直說:“禁旅責司馬徵調失常也。”按古制,保衛王室和都城的武士只負責都城的防務和治安,在一般情況下是不外調去征戰的。但這裡,掌管王朝軍事的祈父——司馬,卻破例地調遣王都衛隊去前線作戰。致使衛士們心懷不滿。從另一角度,我們亦看出當時戰事不斷,兵員嚴重短缺,致使民怨不絕。前人多以為此詩作於西元前789年(周宣王三十九年)王師在千畝受挫于姜戎之時。
全詩三章,皆以質問的語氣直抒內心的怨恨。風格上充分體現了武士心直口快、敢怒敢言的性格特徵。沒有溫柔含蓄的比或興,詩一開頭便大呼“祈父!”繼而厲聲質問道:“胡轉予於恤?靡所止居。”意思是說:“為什麼使我置身於險憂之境,害得我背井離鄉,飽受征戰之苦?”第二章與此同調,但複遝中武士的憤怒情緒似乎在一步步增加,幾乎到了一觸即發的地步。“且自古兵政,亦無有以禁衛戍邊者”(方玉潤《詩經原始》)。武士說:“可你這司馬,卻為何不按規定行事,派我到憂苦危險的前線作戰呢?”作為軍人,本不該畏懼退縮。在國難當頭之際,當飲馬邊陲,枕戈待旦。武士再次質問:“可你這司馬太糊塗了,就像耳朵聾了聽不到士兵的呼聲,不能體察我還有失去奉養的高堂老母。”在第三章裡,武士的質問變為對司馬不能體察下情的斥責。同時也道出了自己怨恨的原因和他不能毅然從征的苦衷。“三呼而責之,末始露情”(姚際恒《詩經通論》)。
對於溫柔敦厚的詩國傳統來說,這首詩似乎有過分激烈、直露的嫌疑,但直抒胸臆,快人快語,亦不失為有特色者。
但或許還能在和親人的依傍中尋求些許暖意,給這充滿傷痛的心以解脫的慰藉和沉醉呢!聽著這來自遠古的動人心魄、直沖雲霄的憤怒悲慟的呼聲,就連今天的人也禁不住為這位生活於亂離之世的詩人的不幸遭遇灑一掬同情之淚了。文學是活的社會生活與心靈體驗的歷史,《小雅-黃鳥》這首詩,正是春秋末葉社會政治腐敗、經濟衰退、世風日下之壞亂景象的一個極具典型意義的縮影。作者在這裡所要表達的是一種不堪忍受剝削和壓榨的憤怒和對世道人心的徹底絕望。
在立意方面,這首詩與《魏風-碩鼠》有異曲同工之妙:即以“啄我之粟”的黃鳥發端,類比起興,以此影射“不可與處”的“此邦之人”,既含蓄生動,又表現了強烈的愛憎感情。
值得注意的是,此詩與《我行其野》,前人多以為出自同時,是周宣王末年禮崩樂壞、社會風氣惡化的表現。王質《詩總聞》論《我行其野》說:“觀此詩,然後知前詩(《黃鳥》)之所以不可與處者也。二詩當出一人。”此說雖未必,但也說明了二詩主題的相關性。舊說如《毛詩序》謂詩旨為“刺宣王”,毛傳雲:“(周)宣王之末,天下室家離散,妃匹相去,有不以禮者”,鄭箋雲:“刺其以陰禮(男女之禮)教親而不至,聯兄弟之不固。”今人多不取。而朱熹《詩集傳》雲:“民適異國不得其所,故作此詩。”差為得之。
《詩經:祈父》
祈父,予王之爪牙。
胡轉予於恤,靡所止居?
祈父,予王之爪士。
胡轉予於恤,靡所厎止?
祈父,亶不聰。
胡轉予於恤?有母之屍饔。
注釋:
1、祈父:周代掌兵的官員,即大司馬。
2、恤:憂愁。
3、靡所:沒有處所。
4、厎:停止。
5、亶:確實。聰:聽覺靈敏。
6、屍:借為“失”。饔:熟食。
譯文:
司馬!我是君王的衛兵。
為何讓我去征戍?沒有住所不安定。
司馬!我是君王的武士。
為何讓我去征戍?跑來跑去無休止。
司馬!腦子的確不好使。
為何讓我去征戍?家中老母沒飯吃。
賞析:
《祈父》是周王朝的王都衛士(相當於後代的御林軍)抒發內心不滿情緒的。《毛詩序》說:“《祈父》,刺宣王也。”鄭箋補充說:“刺其用祈父不得其人也。”朱熹《詩集傳》引呂祖謙語說:“越句踐伐吳,有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皆遣歸;魏公子無忌救趙,亦令獨子無兄弟者歸養。則古者有親老而無兄弟,其當免征役,必有成法,故責司馬之不聰”,“責司馬者,不敢斥王也。”方玉潤《詩經原始》徑直說:“禁旅責司馬徵調失常也。”按古制,保衛王室和都城的武士只負責都城的防務和治安,在一般情況下是不外調去征戰的。但這裡,掌管王朝軍事的祈父——司馬,卻破例地調遣王都衛隊去前線作戰。致使衛士們心懷不滿。從另一角度,我們亦看出當時戰事不斷,兵員嚴重短缺,致使民怨不絕。前人多以為此詩作於西元前789年(周宣王三十九年)王師在千畝受挫于姜戎之時。
全詩三章,皆以質問的語氣直抒內心的怨恨。風格上充分體現了武士心直口快、敢怒敢言的性格特徵。沒有溫柔含蓄的比或興,詩一開頭便大呼“祈父!”繼而厲聲質問道:“胡轉予於恤?靡所止居。”意思是說:“為什麼使我置身於險憂之境,害得我背井離鄉,飽受征戰之苦?”第二章與此同調,但複遝中武士的憤怒情緒似乎在一步步增加,幾乎到了一觸即發的地步。“且自古兵政,亦無有以禁衛戍邊者”(方玉潤《詩經原始》)。武士說:“可你這司馬,卻為何不按規定行事,派我到憂苦危險的前線作戰呢?”作為軍人,本不該畏懼退縮。在國難當頭之際,當飲馬邊陲,枕戈待旦。武士再次質問:“可你這司馬太糊塗了,就像耳朵聾了聽不到士兵的呼聲,不能體察我還有失去奉養的高堂老母。”在第三章裡,武士的質問變為對司馬不能體察下情的斥責。同時也道出了自己怨恨的原因和他不能毅然從征的苦衷。“三呼而責之,末始露情”(姚際恒《詩經通論》)。
對於溫柔敦厚的詩國傳統來說,這首詩似乎有過分激烈、直露的嫌疑,但直抒胸臆,快人快語,亦不失為有特色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