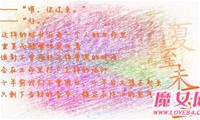《詩經:芄蘭》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
雖則佩觿,能不我知。
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芄蘭之葉,童子佩韘。
雖則佩韘,能不我甲。
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注釋:
1、芄蘭:草本植物,既蘿摩,有藤蔓生。友:同“枝”。
2、覡、:解發結的用具,用象骨製成,供成年男子使用和佩帶。
3、容、遂:指傲慢放肆的樣子。
4、悸:帶子下垂的樣子。
5、揲:拉弓弦的用具,俗稱“扳指”。
6、甲:勝過。
譯文:
芄蘭有枝尖又尖,兒童解錐帶在身。
雖然解錐帶在身,哪裡懂的大人事。
大搖大擺擺架勢,飄帶長垂難收拾。
芄蘭有葉似半圓,兒童扳指帶在身。
雖然扳指帶在身,哪裡有力勝大人。
大搖大擺擺架勢,
賞析:
兒童假裝大人模樣之所以可笑,是不知天高地厚和水深火熱,而天真和稚氣卻是可愛的。大人假裝兒童模樣之所以可厭,是忸怩作態和裝瘋賣傻,讓人疑心他的神經是否有毛病。按這樣的理解,似可把《芄蘭》倒過來看。
裝模作樣需要勇氣、耐心和毅力。本來並非如此,卻要裝作如此,例如生活優裕者裝出滿臉滄桑感的樣子,就要大起膽子把真面目掩蓋起來。為了始終保持某種姿態和形象,比如小白臉作出五尺漢子的姿態,半老徐娘強作少女模樣,就得有耐心和毅力堅持下去,不能讓人看出其中破綻。
啊,這樣的做人、活法肯定很累!每晚回到家中,脫下面具卸下裝,心裡准會嘀咕著一個累字。
當我們在大庭廣眾下見到某些板起面孔、作出某種姿態、拿腔拿調的突出某種形象的人的時候,不妨靜心想想:他或她私下裡是什麼樣子?他或她內心的真實情懷究竟怎樣?
請記住,切不可以貌取人。
《詩經:河廣》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
誰謂宋遠?跂予望之。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
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注釋:
1、河:指黃河。
2、葦:指用蘆葦製成的小筏子。杭:航。
3、歧:踞起腳站著。
4、刀:小船。
5、崇:結束,終結。
6、朝 :上午。
譯文:
誰說黃河寬又廣?一隻葦筏可渡航。
誰說宋國路遙遠?蹄起腳尖可眺望。
誰說黃河寬又廣?一條小船容不下。
誰說宋國路遙遠?一個上午可走到。
賞析:
存在著兩種時間:心理時間和真實時間。
情人分離,度日如年,心理時間遠遠長於真實時間。故國遠隔萬水千山,思念時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歷歷如在目前,心理上的空間遠遠小於真實的空間。我們就是在這一真一幻的時間和空間中生活看,同時存在於內心的世界和真實的世界之中。
黃河雖然寬廣,有時一葉小舟競可飛渡,有時卻容不下一葉小舟。世界很大,有時讓人感到自己渺小得可以被忽略,有時又連一個小小的無名小卒也容不下。心的領域也很大,有時大得可以以容下天地萬物,有時又小得容不下一根針。
浪跡天涯的遊子,面對世界、故鄉、親人,常有這種真、幻交錯的時空感。
《古詩十九首·生年不滿百》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
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
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
愚者愛惜費,但為後世嗤。
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
注釋:
1、“秉”,執也。“秉燭遊”,猶言作長夜之遊。
2、來茲,因為草生一年一次,所以訓“茲”為“年”,這是引申義。“來茲”,就是“來年”。
3、費:費用,指錢財。
4、嗤:輕蔑的笑。
5、“王子喬”,古代傳說中著名的仙人之一。“期”,待也,指成仙之事不是一般人所能期待。
譯文:
一個人活在世上通常不滿百歲,心中卻老是記掛著千萬年後的憂愁,這是何苦呢?
既然老是埋怨白天是如此短暫,黑夜是如此漫長,那麼何不拿著燭火,日夜不停地歡樂遊玩呢?
人生應當及時行樂才對啊!何必總要等到來年呢?
整天汲汲無歡的人,只想為子孫積攢財富的人,
像王子喬那樣成仙的人,恐怕難以再等到吧!
賞析:
人生價值的懷疑,似乎常是因了生活的苦悶。在苦悶中看人生,許多傳統的觀念,都會在懷疑的目光中轟然倒塌。這首詩集以鬆快的曠達之語,給世間的兩類追求者,兜頭澆了一桶冷水。
首先是對吝嗇聚財的“惜費”者的嘲諷,它幾乎占了全詩的主要篇幅。這類人正如《詩經·唐風》“山有樞”一詩所譏刺的:“子有衣裳,弗曳弗婁(穿裹著);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只管苦苦地聚斂財貨,就不知道及時享受。他們所憂慮的,無非是子孫後代的生計。這在詩人看來,簡直愚蠢可笑:“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縱然人能活上百年,
詩人似乎早就料到,鼓吹這樣的放蕩之思,必會遭到世俗的非議。也並非不想享受,只是他們常抱著“苦盡甘來”的哲學,把人生有限的享樂,推延到遙遠的未來。詩人則斷然否定這種哲學:想要行樂就得“及時”,不能總等待來年。詩中沒有說為何不能等待來年。其弦外之音,卻讓《古詩十九首》的另一首點著了:“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誰也不知道“來茲”不會有個三長兩短,突然成了“潛寐黃泉下,千載永不寤”的“陳死人”(《古詩十九首·驅車上東門》)。那時再思享樂,已經晚了。這就是在詩人世間“及時”行樂的曠達之語後面,所包含著的許多人生的痛苦體驗。從這一點看,“惜費”者的終日汲汲無歡,只想著為子孫攢點財物,便顯得格外愚蠢了。因為他們生時的“惜費”,無非養育了一批遊手好閒的子孫。當這些不肖子孫揮霍無度之際,不可能會感激祖上的積德。也許他們倒會在背底裡,嗤笑祖先的不會享福。“愚者愛惜費,但為後世嗤”二句,正如方廷珪所說:“直以一杯冷水,澆財奴之背”(《文選集成》)。其嘲諷辭氣之尖刻,確有對愚者的“喚醒醉夢”之力。
全詩抒寫至此,筆鋒始終還都針對著“惜費”者。只是到了結尾,才突然“倒卷反掉”,指向了人世的另一類追求:仰慕成仙者。對於神仙的企羨,從秦始皇到漢武帝,都幹過許多蠢事。就是漢代的平民,也津津樂道于王子喬被神秘道士接上嵩山、終於乘鶴成仙的傳說。在漢樂府中,因此留下了“王子喬,參駕白鹿雲中遨。下游來,王子喬”的熱切呼喚。但這種得遇神仙的期待,到了苦悶的漢末,也終於被發現只是一場空夢(見《古詩十九首·驅車上東門》:“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所以,對於那些還在做著這類“成仙”夢的人,詩人便無須多費筆墨,只是借著嘲諷“惜費”者的餘勢,順手一擊,便就收束:“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這結語在全詩似乎逸出了主旨,一下子岔到了“仙人”身上,但詩人之本意,其實還在“喚醒”那些“惜費”者,即朱筠《古詩十九首說》指出的:“仙不可學,愈知愚費之不可惜矣”。()只輕輕一擊,即使慕仙者為之頸涼,又照應了前文“為樂當及時”之意:收結也依然是曠達而巧妙的。
這樣一首以放浪之語抒寫“及時行樂”的奇思奇情之作,似乎確可將許多人們的人生迷夢“喚醒”;有些研究者因此將這類詩作,視為漢代“人性覺醒”的標誌。但仔細想來,“常懷千歲憂”的“惜費”者固然愚蠢;但要說人生的價值就在於及時滿足一已的縱情享樂,恐怕也未必是一種清醒的人生態度。實際上,這種態度,大抵是對於漢末社會動盪不安、人命危淺的苦悶生活的無力抗議。從毫無出路的下層人來說,又不過是從許多迷夢(諸如“功業”、“名利”之類)中醒來後,所做的又一個迷夢而已——他們不可能真能過上“被服紈與素”、“何不秉燭遊”的享樂生活。所以,與其說這類詩表現了“人性之覺醒”,不如說是以曠達狂放之思,表現了人生毫無出路的痛苦。只要看一看文人稍有出路的建安時代,這種及時行樂的吟歎,很快又為憫傷民生疾苦、及時建功立業的慷慨之音所取代,就可以明白這一點。
至於那些孜孜追索于藏金窯銀的守財奴,聽了更要瞠目咋舌。這些是被後世詩論家歎為“奇情奇想,筆勢崢嶸”的開篇四句(方東樹《昭昧詹言》)。它們一反一正,把終生憂慮與放情遊樂的人生態度,鮮明地對立起來。詩人似乎早就料到,鼓吹這樣的放蕩之思,必會遭到世俗的非議。也並非不想享受,只是他們常抱著“苦盡甘來”的哲學,把人生有限的享樂,推延到遙遠的未來。詩人則斷然否定這種哲學:想要行樂就得“及時”,不能總等待來年。詩中沒有說為何不能等待來年。其弦外之音,卻讓《古詩十九首》的另一首點著了:“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誰也不知道“來茲”不會有個三長兩短,突然成了“潛寐黃泉下,千載永不寤”的“陳死人”(《古詩十九首·驅車上東門》)。那時再思享樂,已經晚了。這就是在詩人世間“及時”行樂的曠達之語後面,所包含著的許多人生的痛苦體驗。從這一點看,“惜費”者的終日汲汲無歡,只想著為子孫攢點財物,便顯得格外愚蠢了。因為他們生時的“惜費”,無非養育了一批遊手好閒的子孫。當這些不肖子孫揮霍無度之際,不可能會感激祖上的積德。也許他們倒會在背底裡,嗤笑祖先的不會享福。“愚者愛惜費,但為後世嗤”二句,正如方廷珪所說:“直以一杯冷水,澆財奴之背”(《文選集成》)。其嘲諷辭氣之尖刻,確有對愚者的“喚醒醉夢”之力。
全詩抒寫至此,筆鋒始終還都針對著“惜費”者。只是到了結尾,才突然“倒卷反掉”,指向了人世的另一類追求:仰慕成仙者。對於神仙的企羨,從秦始皇到漢武帝,都幹過許多蠢事。就是漢代的平民,也津津樂道于王子喬被神秘道士接上嵩山、終於乘鶴成仙的傳說。在漢樂府中,因此留下了“王子喬,參駕白鹿雲中遨。下游來,王子喬”的熱切呼喚。但這種得遇神仙的期待,到了苦悶的漢末,也終於被發現只是一場空夢(見《古詩十九首·驅車上東門》:“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所以,對於那些還在做著這類“成仙”夢的人,詩人便無須多費筆墨,只是借著嘲諷“惜費”者的餘勢,順手一擊,便就收束:“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這結語在全詩似乎逸出了主旨,一下子岔到了“仙人”身上,但詩人之本意,其實還在“喚醒”那些“惜費”者,即朱筠《古詩十九首說》指出的:“仙不可學,愈知愚費之不可惜矣”。()只輕輕一擊,即使慕仙者為之頸涼,又照應了前文“為樂當及時”之意:收結也依然是曠達而巧妙的。
這樣一首以放浪之語抒寫“及時行樂”的奇思奇情之作,似乎確可將許多人們的人生迷夢“喚醒”;有些研究者因此將這類詩作,視為漢代“人性覺醒”的標誌。但仔細想來,“常懷千歲憂”的“惜費”者固然愚蠢;但要說人生的價值就在於及時滿足一已的縱情享樂,恐怕也未必是一種清醒的人生態度。實際上,這種態度,大抵是對於漢末社會動盪不安、人命危淺的苦悶生活的無力抗議。從毫無出路的下層人來說,又不過是從許多迷夢(諸如“功業”、“名利”之類)中醒來後,所做的又一個迷夢而已——他們不可能真能過上“被服紈與素”、“何不秉燭遊”的享樂生活。所以,與其說這類詩表現了“人性之覺醒”,不如說是以曠達狂放之思,表現了人生毫無出路的痛苦。只要看一看文人稍有出路的建安時代,這種及時行樂的吟歎,很快又為憫傷民生疾苦、及時建功立業的慷慨之音所取代,就可以明白這一點。